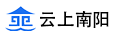一场婚礼,新娘子在半路上跟迎亲的其他男人跑了,是什么原因?三个亲如兄弟的发小,却走向不同的人生轨迹,是什么造成的……
“这场起源于贫穷、最终致富奔小康,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,时时提醒我,身处这个伟大时代,一定要把这些写下来。每个小人物,都是伟大时代的奋进者和创造者,今天,仍然需要他们投身、奉献这个伟大的时代。”长篇小说《三山凹》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,作家李天岑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。
记者:《三山凹》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,为什么要创作这部小说?
李天岑:南阳西峡县一个企业家朋友和我聊天,说村里有三个虎年出生的兄弟比着干,比谁生意做得好、日子过得好。三个发小,是我思考创作的萌芽。但故事,却来源于我的身边经历。
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,出生在穷乡僻壤,小时候住的是野草和泥混搭的房子,常年吃红薯,最差的一年平均一人只分到十八斤小麦,穿衣服补丁不断,很多细节都写在小说里,我亲身体验到父老乡亲不仅解决温饱问题,还过上富裕的生活。如今村子里,公路修到家门口,公交站就在村边,铁路离村子就两里路。村民们开小汽车、骑摩托车,办各种企业,大学生越来越多,文化素质都越来越高。
这一切让我不得不拿起笔来讴歌这个时代,表现改革开放和脱贫攻坚给农村带来的巨变,表现农村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。
《三山凹》以三个发小为原型,从改革开放前夕一直写到2019年,讲述他们的成长、困惑、拼搏,这既是个关于友情、乡情乃至大情义的故事,反映农民兄弟身上憨厚朴实的特质和励志奋进的不屈;又是个农村改革史的故事,是几个共产党员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分镜头。这些故事,都是时代的产物。我很幸运,创作时就像穿越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隧道,这些人物总是跳出来,逼得我不得不写。
记者:虽是写三个发小,但作品构建的空间和时间维度都足够大,这种难度怎么克服?
李天岑:三个发小,是农民、企业家、官员,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,但围绕他们身上的主线一直是改革开放和脱贫攻坚。虽是从三山凹村写起,但故事同时串联起黄龙镇、丰和县、南都市到深圳的故事,从乡村到县城到改革前沿,实质上反映了城乡互动、全国改革一盘棋逐步深化的历程。
改革开放的目标,是让中华民族脱贫,使国家由穷到富、由富到强。这本身就是一场摆脱贫困的斗争,给脱贫攻坚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脱贫攻坚着眼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,让人民过上好日子。这反映了我们党一脉相承的为民初心和久久为功的实干精神。这条主线牢牢树在这里,就牵引着故事的走向。
比如柳大林,作为一个从农民中走出来的有知识、有理想、有情怀的官员,面临很多世情的困惑,但他做出坚守和选择,始终保持为民服务的初心和公心。再比如有情有义朴实上进的张宝山,以及很多出场不多的小人物,他们的戏都紧紧聚焦主线,正是因为这代人的奋进,才有了改革开放和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变。
记者:您经历过农民、工人、官员多种身份,为什么您的很多作品都始终聚焦农村?
李天岑:这些年我写了很多作品大多聚焦在农村,不光是因为我出生、熟悉农村,更因为农村值得深刻研究。农村始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,从小岗村改革到现在,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。在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后,下一步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,任何道路都需要艰辛探索,农村还要做好产业、组织、人才的振兴。农村还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重要地段。
这部作品是中国作协2020年度脱贫攻坚奔小康重要题材的重点扶持作品,还获得了十二届小说选刊的年度大奖,也体现了文艺界对这样题材的认可和重视。这些年,我发现身边的作家朋友越来越写实,越来越把笔端触及广大农村以及脱贫攻坚。比如《暖夏》《乡村第一书记》《大地》等一批写农村、脱贫攻坚的作品。如果说过去有赵树理的山药蛋派、孙犁的荷花淀派,在这个时代,也会有这样一种趋向,出现一批反映农村巨变、脱贫攻坚的,也许该称之为“新的乡土文学派”,这对农村、对时代来说都是大好事。
记者:时间跨度大,又是农村题材,您希望年轻人怎么读这部小说?
李天岑:年轻人读纸质书少了,不在于他们不喜欢读小说,而在于缺乏像当年《青春万岁》《暴风骤雨》等一批优秀作品,现在的作家担负的使命更重。
我的写作是开放式的写作,我边写边跟很多人交流,和50后、60后、70后、80后、90后乃至00后,我都问他们的意见。张宝山的形象前几章写得有人觉得单薄,后来塑造张宝山的时候,我就加大了他的分量,由一个普通农民变成积极入党带领大家一起致富,形象更为丰满。比如,最终成书的封面设计方案有两个,我一共发给不同年龄阶段31个人,结果两种方案一半对一半,我就把一个做了封面,一个做了封底。
小说结尾我写了一首山歌,“玫瑰花儿开满山”“小康日子比蜜甜”,这是历经风雨之后才能收获的别样人生。今天,为了人民更美好的生活,还要把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。美好的未来要靠年轻人,我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读到这本书,汲取前人的智慧、勇气和担当,心怀梦想、脚踏实地,在时代的舞台上大放光彩。
新华社 记者:王敏 编辑:冯筱晴